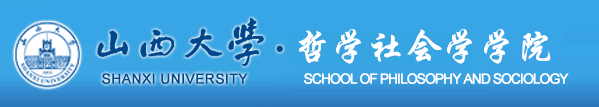“自我反省、独立思考”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杜镇远教授《他山之石》出版感怀
北京大学哲学系 聂锦芳

谨向杜镇远老师致敬!昨晚和今天见到这么多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内心很激动,同时也更加怀念已经去世的张恩慈老师。这几年我写了很多东西,但没有写出对张老师的追忆和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曲折命运的思考,这是我的“罪过”和心结!
虽然阅历上与在座的老师相比仍然浅了些,但仔细清点一下发现,我是你们30年前的学生,现在也已经年过半百,到了鲁迅写作《朝花夕拾》的年纪了。有的老师可能知道,今年我的研究工作到了一个关节点:耗费了我20年心血的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出版了。这期间有很多杂志和报纸约稿,我借此机会也认真回顾和总结了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那么,在山大学习7年之于我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我能想到的与杜老师相关的有两点:
一是外语学习。我是1985年入学的,那时中苏关系开始缓和,在系里当政的杜镇远老师和武高寿老师做出了一个可能除我而外我们班50多位同学都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学习俄语。我们是从零基础开始的,一般大学外语只开设两年,但外语系的孟老师和郑老师却自愿带着我与康有、秀生等学了6年!靠此奠定的基础,到人民大学后我才从俄文资料中知道,马克思著述是一个庞大的文献王国,他享年65岁,写作生涯长达50年,而且几乎没有中断过。但他写下来的作品中,成型、定稿的很少,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笔记、摘录、提纲、草稿和过程稿。对于一个思想复杂的人来说,其观点的复杂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定稿的部分和表述明确的段落中,更可能蕴含在对这些观点的探索和论证中。而哲学探索和研究的关键也就在于论证。我更进一步了解到,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并不是完全按照马克思原始手稿编辑的,而是由苏联文献专家根据当时特殊情况下的理解对手稿做了不少更动后整理而成的,而且经过了文字上德—俄—中文的转换。至此我才明白,对于马克思研究来说,回到原始文本、文献是多么重要和必要!这种信念支撑了我20年来几乎全部的研究工作。现在设想,如果我当初学习的是英语,并且以后也在从事学术工作,很可能会选择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实际上在中国是不缺乏这方面的人的,但另一方面离奇的情况是,在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从事文本、文献研究的却屈指可数!这样说来,我今天的状况就与杜老师他们当年那个“错误”的决定很有关联了,为此我对他们心存感念之情!
第二个方面与北大有关。当年的条件肯定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但那时哲学系有个好的做法和传统,就是规定研究生期间必须外出访学两次,系里提供经费。我和康有到北京访学是杜老师带着去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魏公村国家图书馆招待所安顿下来后,杜老师先独自去北大拜访他的老师黄枏森先生和他的同学叶朗教授。在拜会结束时他征求黄老师的意见,说有两个学生想见见您,是否可以。黄老师虽然德高望重,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但极其平易近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和康有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黄老师居住的中关园,黄老师在他那间由于堆满图书资料而显得很狭小的书房接待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我在人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有机会来到北大工作,并且成了黄老师的同事。现在想起这些往事,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谈到与北大的关联,必须提到今天我们研讨的杜老师新著《他山之石》后记中的一句话——“自我反省,独立思考”。我觉得,这是北大的传统、哲学的要义,也是这本书的精髓。哲学的进步有赖于哲学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式的转换。这部书是根据杜老师20年前授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所涉及到的各个板块和具体流派在近年学界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这些进展是奠基于像杜老师这样的思想解放的理念之上的。杜老师这代人从灾难深重、思想炼狱中走过来,我都能体会到当年张恩慈老师、余维综老师和杜老师这些人被迫离开北大、离开北京、流落到并非其故土的山西时苍凉的心境。从磨难中走出来的杜老师最切近的感受,就是必须决然地告别人云亦云、麻木追从的路数和思维,独立地进行思考,理性地看待世界。他强调哲学的科学基础,致力于哲学与科学的结合与联盟;而在我看来,更深刻地见解在于,把马克思放到西方思想发展中进行的讨论,认为不理解西方哲学史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可悲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即使在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没有成为共识,不在少数的论者把马克思与西方思想割裂开来进而对立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对抗西方思潮和社会。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不少论者还在报刊上宣扬和阐述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念,表征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多么艰难!这也表明,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是多么重要和迫切!

这里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张恩慈老师退休后的选择。在中国,一个人的思考在其公开发表的东西中并不能得到完整地体现,张老师的情况就是如此。我是张老师的最后一个学生,送走我之后他就退休了。这时他的选择是不再从事所谓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他没有沉浸在那部大部头的《认识论原理》的荣耀中,更很少提及六十年代他所发表的论文造成的轰动效应和那部《认识与真理》的小册子翻译成多种外文,相反,他想将过去的那些业绩彻底忘掉。他对肖前教授说:以后开会我们就不要发言了,没有新东西讲什么呢?尽量让年轻人讲吧。他是很少向学生流露情感的,但我回去看他时他说的两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次谈到北京学界的状况,他不再注视我,而是把目光转向窗外,停顿了一下后说:我回不去了!另一次,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我们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但从来没有到过他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多年后,我受邀到了特里尔,在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工作了一年,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每当我下班在布吕肯大街出来的广场边上等车回家时,遥望那些耸立着的古罗马宫殿和巴洛克建筑,浏览风景如画的摩泽尔河畔风光,无限地感叹:这块土地上酝酿、培育的理论和学说怎么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威权专制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中的单线论?于是,我心里一再回味起张老师那些话的深意和他晚年选择的价值。
发言规定的时间到了,再次祝贺杜老师大作的出版,感谢老师们的培养!